
用最专业的眼光看待互联网
立即咨询>我每晚都梦见同一场扑克牌局,
>直到某天在现实聚会里发现参与者、座位顺序甚至每张手牌都和梦里一模一样;
>当最后一张牌即将发出时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
>无论输赢,梦的结局都是所有人同时掀开底牌后惊恐尖叫着消失。
又来了。
不是模糊的碎片,也不是醒来即褪色的褪色的水印。是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地下室陈年灰尘与廉价雪茄混合气味的真实,是绿色绒布桌面上那圈刺眼台灯的光晕,是指尖划过扑克牌边缘那种微涩的触感。每晚,准时准点,像一盘精心录制又被无数次循环播放的录像带。
四个人。永远是四个人。
我对面是靠倒卖各种批文发了点小财的老王,腆着的肚子快要抵住桌沿,油光满面,手指上那枚金戒指在灯下晃得人眼晕。左手边是刘教授,总是一丝不苟地穿着件半旧的中山装,眉头习惯性地锁着,像是永远在思考什么难题,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右手边,是小曼,年轻,漂亮,带着点恰到好处的懵懂,眼神却偶尔会掠过一丝与她年龄不符的精明。
还有我。一个旁观了无数遍,却始终无法介入剧情的木偶。
牌局在沉默中进行,只有纸牌滑过绒布的沙沙声,以及筹码被推出去时沉闷的撞击声。我知道老王会在一开始就用一对K吓退小曼,知道刘教授会在第三轮弃牌时下意识扶一下他的金丝眼镜,知道小曼会在只剩下我和老王时,用她那涂着丹蔻的指甲轻轻敲击她那张决定性的黑桃A。
一切都像是用刻度尺量过,用秒表掐过。分毫不差。
我试过在梦里大喊,试过猛地掀翻桌子,试过在老王打出那张K之前就指出他的底牌。但没用。声音像是被吸进了黑洞,动作迟缓得如同陷在深海泥潭。我只能看着,一遍,又一遍。���后,在最后一张牌——那张该死的,我从未看清过的河牌——即将被虚拟的荷官发出的前一刻,景象开始扭曲,所有人的脸在惊愕中变形,化为一片炫目的白光和无声的尖啸。
惊醒。一身冷汗。心脏擂鼓。
起初以为只是压力太大。我去看了医生,做了检查,甚至还尝试了催眠。结果一切正常。“可能是某种既视感的强化,放轻松,别太在意。”医生轻描淡写。
可我没办法不在意。那梦太具体,太顽固,像一根楔入大脑的冰冷钢针。白天的一切都仿佛隔了一层毛玻璃,唯有夜晚那几十分钟十分钟的地下室牌局,清晰得令人窒息。
直到李总的那个电话。
一个普通的商业合作对象,项目谈成后的私人性质庆祝,地点在他名下的一处郊区别墅。“带几个朋友,随便玩玩,放松一下。”
我没多想。直到司机把车停在那栋带着巨大花园的独栋别墅前,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了上来。太熟悉了,不是因为李总发来的照片,而是……另一种更幽深的原因。
保姆引着我穿过铺着厚地毯的走廊,推开一扇沉重的橡木门。光线骤然变暗。
心跳漏了一拍。
不是宽敞明亮的客厅,而是一个装修考究,但明显带有私密性的房间。厚重的窗帘遮住了外面的天光,房间中央,一盏吊灯投下昏黄的光晕,精准地笼罩着一张墨绿色的扑克桌。
四个人影在灯光下抬起头。
时间仿佛瞬间凝固,又被一只无形的手粗暴地捏碎。
老王。刘教授。小曼。
他们穿着和梦里一模一样的衣服,脸上挂着同样模式化的微笑。老王拍了拍他旁边的空位:“就等你了,来来来,坐这儿!”
那个位置。我的位置。
一股冰冷的麻痹感从脚底直冲头顶。我僵在原地,喉咙发紧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是巧合?不可能。这世界上没有如此严丝合缝的巧合。每一个细节,每一道阴影,甚至是空气里漂浮的雪茄烟味(李总并不抽烟),都和我夜夜经历的噩梦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。
“怎么了?脸色这么难看。”小曼歪着头,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。
我强迫自己移动脚步,几乎是跌坐进那张高背扶手椅。绒布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裤料传来,和梦里一般无二。
牌局开始了。
李总兼任了荷官,他熟练地洗牌、切牌、发牌。动作流畅,带着一种表演式的优雅。我看着他的手,看着那些扑克牌如同被设定好程序的蝴蝶,一张张精准地落在我们面前。
底牌。我不用看。
一张方块8,一张草花J。和梦里一样。
我抬起头,目光从老王志得意满的胖脸,移到刘教授紧抿的嘴唇,再落到小曼那双看似无辜,实则暗藏锋芒的眼睛上。他们的每一句闲聊,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,每一次筹码的摆放,都在无情地印证着那个预定的剧本。
我不是在做梦。这一次,我的身体沉重,掌心出汗,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。这是现实。残酷的、不容置疑的现实。
牌局在进行。翻牌,转牌……公共牌一张张亮出。桌上的筹码在缓慢流动,对话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,内容空洞乏味,和我记忆中(或者说,预知中)的台词一字不差。
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,越收越紧。我不再试图反抗这流程,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等待,等待那个最后的时刻。那个我从未亲眼目睹,却用身体牢牢记住的终结。
终于……到了最后。
台面上已经堆起了可观的筹码。只剩下我和老王还在牌桌上。小曼和刘教授早已弃牌,此刻正屏息凝神地看着我们俩。按照剧本,老王的明牌是一对Q,而我的,是顺面。他下了一个重注,嘴角咧开,金牙闪闪光。
该我说话了。
按照剧本,我应该跟注,然后等待最后一张河牌。
房间里静得可怕,连空调出风的微弱声音都消失了。吊灯的光晕似乎也收缩了一些,更加集中地投射在绿呢桌面上,那方寸之地亮得刺眼。
李总的手指,已经搭在了牌摞最上面那张牌的边缘。只要轻轻一推,那张决定命运的河牌就会滑出。
就是现在!
梦境的终点!那张牌出现前的一瞬!
我的瞳孔猛地收缩。一直以来,困扰我的不仅仅是重复的梦魇,更是那个结局。无论牌面上谁输谁赢,在梦的尽头,当最后一张牌发出的指令下达,但牌还未完全显现的刹那——所有人,包括荷官,都会同时做出一个动作:猛地掀开自己的底牌!
然后,不是胜利的欢呼或失败的叹息,而是整齐划一的,极度惊恐的尖叫。紧接着,所有人的身影就像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,剧烈闪烁几下,瞬间湮灭,消失在炫目的白光和撕裂耳膜的无声尖啸中。
那不是赌局的结束。
那是存在的终结。
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。我明白了,这场牌局根本无关金钱,无关胜负。它是一个仪式,一个开关。而我们现在,正站在那个开关的边缘,手指已经按了下去,只差最后那一点点压力。
李总的手指微微一动,那张河牌的边缘即将脱离牌摞。
不!
我不能让它发生!
悟空德州最新下载链接我猛地张开嘴,想喊“停下”!想告诉他们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!想掀翻这张该死的桌子!
可喉咙像是被水泥堵死,声带振动,却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。只有嗬嗬的气流。
老王、刘教授、小曼,他们的眼神空洞,嘴角却挂着诡异的、凝固的微笑,仿佛三尊涂了油彩的木偶。他们的手,都已经不约而同地,用一种极其缓慢但又无比坚定的动作,移向了自己那两张始终覆盖着的底牌。
李总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我,那眼神深处没有任何人类的情绪,只有一片漠然的、程序执行前的确认。
他的手指轻轻一送。
那张牌,带着宿命的弧度,开始向桌面滑行。
时间被无限拉长。
我看到老王肥胖的手指已经抠住了底牌的边缘。
看到刘教授的眼镜片上反射着惨白的光。
看到小曼鲜红的指甲按在了牌背上。
完了。
这个念头如同冰锥,刺穿了我所有的挣扎。
无论我做什么,无论我跟注、加注还是弃牌,结局都已注定。梦早已昭示,唯一的变数,只是我清醒地、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。
在极致的恐惧和绝望中,一种诡异的冷静反而浮现出来。我放弃了抵抗,甚至不再去看那张正在滑向命运终点的河牌。我的目光,死死锁定在那四双即将掀开底牌的手上。
来吧。
让我看看,那底牌之下,究竟是什么,让我们所有人,都惊恐至此,万劫不复。
那张河牌,带着一种慢得令人心脏骤停的优雅,旋转着,飘向桌面中央那片被灯光烤得炽热的绿绒。它的背面,统一的蓝色鸢尾花图案,像一个永恒的、冷漠的封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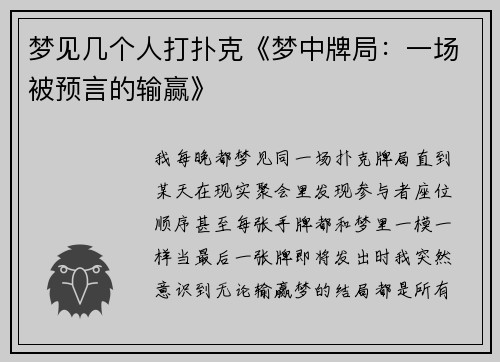
几乎在同一时刻。
老王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而用力的闷哼,他那戴着金戒指的粗壮手指猛地一掀!
刘教授的动作则带着一种学者式的决绝,指尖因用力而失去血色,啪地将两张牌同时挑起。
小曼涂着丹蔻的指甲像是两道血痕,划开了牌背的宁静。
我的手,不受控制地,或者说,是被一种远超我自身意志的力量牵引着,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动作——狠狠将面前那两张覆盖了整晚,象征着未知与可能的纸牌,摔在了桌面上!
视线在千分之一秒内聚焦。
我的底牌,方块8,草花J。意料之中。
老王的底牌,红桃Q,黑桃Q。四条Q。毫无悬念的巨大牌面。
刘教授的底牌,一对3。早已弃牌的正确选择。
小曼的底牌,黑桃A,黑桃K。同花顺的胚子,可惜……
这些牌面,这些输赢,在这一刻,突然变得毫无意义,渺小得可笑。就像狂风巨浪中计较一滴水珠的形状。
真正的惊骇,来自于底牌之下的东西。
就在牌背被掀开,牌面数字暴露在灯光下的那一瞬间——
每一张扑克牌的正面,那原本应该是红色或黑色的桃心、方块、梅花、黑桃图案的地方……出现的,不是符号。
是影像。
是极度清晰,纤毫毕现,仿佛透过一个小窗看到的实时景象。
在我的草花J上,我看到的是——我自己。正是此刻,坐在这个座位上,瞳孔放大到极致,面部肌肉因极致恐惧而扭曲的,我自己。视角是从正对面,略高的位置拍摄的,像一个冷酷的监视器。
猛抬眼,看向老王的红桃Q。牌面上,映出的正是老王那张布满油汗、惊骇欲绝的脸,背景是这间房间,这张桌子。
刘教授的方块3上,是刘教授扶着眼镜框,手指僵硬定格的模样。
小曼的黑桃A上,是她自己那张写满无法置信的俏脸。
每一张底牌,都像一面镜子,精准地、实时地映照出持牌者在此刻,此分,此秒,最真实的恐怖表情。
但这还不是全部。
当我们因为眼前的异象而本能地转动眼球,看向对方甩出的其他底牌时——
在老王的黑桃Q上,我看到的是小曼的侧脸。
在刘教授的另一张方块3上,映出的是老王肥硕的后脑勺。
在小曼的黑桃K上,是我因过度震惊而微张的嘴。
交叉,嵌套,无限循环。
我们看到的,不是静止的照片,而是动态的、实时的反馈。就像一个由无数面镜子构成的迷宫,每一面镜子都在反射其他镜子的影像,层层叠叠,永无止境。而所有这些影像的核心,都是我们四人此刻极致的恐惧。
这诡异的镜像地狱抽干了房间里最后一点空气。
“呃……”
第一个声音来自老王,那不是人类语言,更像是气管被割开后漏气的嘶鸣。
随即,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。
四张嘴巴同时张开到了极限,喉咙肌肉绷紧如岩石,四条声带以相同的频率剧烈震颤——
“啊————————!!!!!”
尖叫声爆发了。
不是一声,而是四声叠加、共鸣、扭曲在一起的恐怖合奏。它尖锐得能刺穿鼓膜,又浑厚得仿佛来自地心深处。声音里裹挟着足以摧毁理智的惊骇,一种看到了绝对不该看之物的、源自生命本能的绝望嘶嚎。
在这非人的尖叫声达到顶峰的刹那,吊灯的光线骤然变得无法形容的炽白。
不是灯泡烧毁的那种白,是一种吞噬一切色彩、一切形态的纯白。光线如同有质量的液体,瞬间灌满了整个房间。
桌子,椅子,筹码,扑克牌……所有的一切,包括我自己的身体,都开始失去实体感。边缘变得模糊,像是在高温下熔化的蜡像。
视觉被剥夺,只剩下一片虚无的白。
听觉里也只有那持续撕裂的尖叫,甚至盖过了我自己发出的声音。
然后,我感觉自己在“溶解”。不是疼痛,而是一种存在感的急速流失,仿佛构成“我”的物质正被分解成最基本粒子,投入那片白色的混沌。
最后的意识,捕捉到的不是景象,不是声音,而是一个无比清晰的认知,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灵魂上:
那底牌映出的,不是我们的脸。
是“它”,正在通过我们的眼睛,看着我们自己。
白光彻底吞没了一切。
寂静。